抱歉,我不能如你所願
下午四點去接小孩放學。
大兒子看到我劈頭就說:「5點再來接我,我要去跟同學打籃球。」
我思考了幾秒鐘,告訴他:「我出門前煮了飯,剛剛去繳費、又去超市買牛奶,還去市場買了菜。我現在載弟弟回家就4點半了,打算開始做菜,如果一下子又要出門接你,太累了,我不要。」
他想了一下,說:「那我打完球,自己走路回家。」
雖然我的腦中閃過了5點後車子多,走過正在修橋的便道有些危險,但我還是回答:「好的,你路上要小心。」兒子把書包放到車上,一溜煙就跑走,打球去了。那一天,他5點半左右自己走路回到了家。
雖然,對孩子的愛是無條件的,但是我們能給的仍是有「限度」的。我常常提醒自己,做自己能力範圍可以做到的,不要為孩子「犧牲」,不讓孩子欠我「人情」。在孩子的照料上是如此,在滿足孩子的需求上也是如此。
或許這是從父母那裡學來的。記得小學的時候,很羨慕跳芭蕾舞的同學,跟母親說我也想學,母親問過價錢後,鄭重地告訴我,家裡沒有餘裕;第一次到同學家看到鋼琴、觸摸到鋼琴也好生喜歡,但家裡無法負擔昂貴的學琴和買琴費用。當父母說:「不行、不能或不可」時,還是孩子的我,當然失望,也覺得難過,但是我知道父母說的是事實,所以並沒有怨懟。現在回想起來,我很感謝父母讓我知道,為人父母盡力、盡量就好。
前一陣子,有個朋友快當爸爸了,他很焦慮地問我:「養一個孩子要多少錢?」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想過,也沒計算過的問題。我總覺得給孩子足夠的陪伴、足夠的傾聽、足夠的愛,並且做孩子生活上的榜樣,才是最重要的。兩個孩子沒有上安親班,也沒補習,因為沒興趣,也沒有上任何才藝班;我也從來不幫他們買名貴的衣服或奢侈的玩具,對我來說,養兩個小孩,在國民教育的階段,並不會「太花錢」。
保險的業務員幾次極力說服我要幫孩子儲蓄教育基金、買保險,我也意興闌珊。我只做了自己基本的保險規劃,但我並不認為孩子將來唸大學或出國唸書,是我必須負擔的、責無旁貸的義務。如果我有能力,當然會支持孩子,如果到時候不是如此,孩子應該可以自己想辦法。我希望我的陪伴和守護,能帶給他們豐富的生命力和獨立自主的能力,但是並不熱衷為他們的未來造橋鋪路。
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契約
記得我翻譯的『我的漫畫人生』一書中,日本漫畫之神手塚治虫提到自己對孩子的教養時,也舉過類似的例子。手塚表示自己很少直接管教小孩,大部份都是妻子在操勞。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的兒子小二或小三時,正在收集一組超人和怪獸的玩具,ㄧ直吵著要買還沒收集到的,手塚於是帶著孩子出門,到新宿和神田ㄧ帶的玩具店一家、ㄧ家找。結果走遍了店家,還是沒有找到,他們很失望地回到家。 手塚認真地對孩子說:
「我為了你,總之是花了這麼多的時間,到處走、到處找。雖然沒有找到,可是為了你,已經盡了全力,盡了我的義務了。這回該你聽我的了。玩具你就死心了吧。聽好,你要別人為你做什麼的時候,也要想到你要為別人做什麼來回報。」
手塚的兒子親眼看到父親盡力去幫他找玩具,雖然沒有找到,但也願意放棄,不再吵鬧。手塚表示,「我的那些話的用意是要和他定下契約。我認為,那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契約,而不是父母親對小孩子單方面的強制行為。」
手塚的與孩子之間「平等的契約」,讓我聯想到宮崎駿導演的『崖上的波妞』中的親子關係。
五歲的孩子也能說理
宮崎駿的動畫常常喜歡以孤兒或是「暫時性孤兒」(如『神隱少女』中的千尋)當主角,不重視父母親的角色,特別是母親常常缺席(如『龍貓』);然而在『崖上的波妞』中,宮崎駿第一次正面描寫「母親」這個角色。可能是主角宗介是五歲的小男孩吧!再怎麼說,讓五歲的小孩「無父無母」一個人冒險,太脫離現實。不過,這一次,是父親缺席,宗介的父親是船長,整部片中都在海上,不能參與宗介的奇遇與大冒險。
看過『崖上的波妞』的朋友,一定覺得很奇怪,在片中,宗介叫母親「理莎」,叫父親「耕一」,也就是直呼其名。研究所的同學問我,這是日本人的習慣和常態嗎?當然不是。其實,這個部份連日本觀眾自己看了都有違和感,為什麼彬彬有禮的宗介,會跟老師打招呼、會得宜地跟老人照護中心的老婆婆們應對進退的小男孩,竟然「沒禮貌」地直呼父母的名字?
我想,宮崎駿在這裡試圖建構一種理想的、「對等、如朋友般」的親子關係。而名字的稱呼,正是這種關係的體現。
片中,發生大海嘯之後,理莎載著宗介回到崖上的住家,遇到了從魚變成人類的波妞。在安頓好宗介和波妞之後,理莎看到山上還有路可以通往她工作的老人照護中心,於是用車子載了毛毯和食物,打算一個人去探望留在院裡的老人們。理莎告訴宗介自己的打算,並且要求宗介和波妞留守家裡。
來回味一下這段對話:
宗介:「我也要去。帶波妞ㄧ起去就好了。」(波妞那時已經睡著了)
「我要跟理莎一起去!」
理莎:「宗介呀,現在這個家就是暴風雨中的燈塔。在黑暗中的人們,
大家都因為這裡有燈火而受到鼓舞。所以,一定要有人守著這裡。」
「發生了很多不可思議的事,現在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「不過,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知道吧!我現在擔心在『向日葵』的人。
宗介如果能守住這裡,會讓理莎更有勇氣。不要擔心,我一定會回
來。」
宗介:「一定?」
理莎:「一定!」
宗介:「一定喔!」
理莎:「我愛宗介。」
說完,理莎就開車走了。
在故事的安排上,這樣一來,宮崎駿就順理成章讓宗介和波妞變成「暫時性孤兒」,在沒有大人的庇護下,得以展開接下來的冒險。
然而,以現實的層面來看,一位母親在那樣緊急、未知的情境下,撇下五歲的小孩,自己去救人,是有些不合情理。當然,宮崎駿在此鋪陳了崖上住家在大海嘯淹沒城鎮後,仍因為獨立的維生系統,處在有水、有電、有瓦斯的狀態,是觸目可及的範圍內,唯一安全又溫暖的地方。所以,理莎把孩子放在安全的地方,去可能有危險的老人照護中心送物資,並非不可理解。但是,如果宗介是一個只會哭鬧、死黏著母親的孩子,這樣的劇情是不會有說服力的。
說到這裡,我們就會察覺,宗介稱呼媽媽「理莎」,叫爸爸「耕一」的設定是多麼地巧妙。這對夫妻不遵循一般日本的教養常規,另類地要孩子叫他們的名字,是試圖和孩子建立對等的、朋友般的關係。
當理莎告訴兒子:「宗介如果能守住這裡,會讓理莎更有勇氣」時,她不是高高在上以大人對小孩的權威在說話,而是以互相依存的夥伴口氣在商量。
尊重孩子的個體性,也讓孩子學會尊重父母
這樣的對等關係,只可能建立在「孩子是ㄧ個獨立的個體」的前提之下,而非父母的身、心、意識的延伸。先尊重孩子的個體性,才能讓孩子學會尊重父母的思考和決定,而非要求孩子屈就臣服父母的權威。或許說起來容易,做起來難吧!畢竟像宗介這樣可以說理的五歲小孩並不多見。
我想起兩個孩子還在幼稚園時,ㄧ帶他們進便利商店,他們低矮的視線常常會「搜尋」到誘人的小玩具、或是愛吃的巧克力,然後興高采烈地拿著「獵物」到收銀台要去結賬。我會告訴他們:「那不是媽媽現在要買的東西,如果你們要,只能拿10元以下的。」他們看了看標價,知道「太貴了」,就自動把東西放回去。找不到十元以下喜歡的東西,就放棄。
或許,就是這樣,先學會理性地跟孩子說:「不」吧!讓孩子知道,「我愛你,但抱歉,我無法滿足你所有的慾望。」*
文/攝影:游珮芸
台大外文系畢業,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。出生在台北,旅居東京、京都11年,旅行過世界20多國,現在落腳台東,在自己建立的小窩和兩名前世的情人同居。
任教於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,愛聽童話(兒童說的話),喜歡攝影、畫畫,也寫詩。
本文已刊載於『兒童哲學月刊』No.16 ( 2012.05 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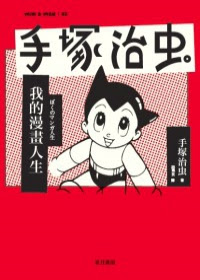

1 則留言:
與孩子平等平權觀念建立,傾聽和支持孩子心聲與願望,塔起家庭教育功能,在學習中使孩子知道如何學習。這樣已經給孩子百分之百的愛了,還須要什麼其它呢?
張貼留言